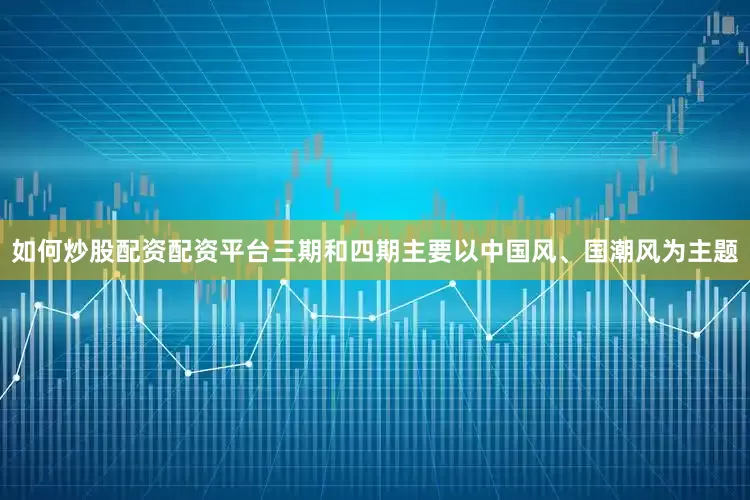公元前 47 年深秋的清晨,长安未央宫前殿笼罩在一片肃杀中。70 岁的前将军萧望之颤抖着接过皇帝特使送来的鸩酒,仰天长叹:“吾尝备位将相,年逾六十矣,老入牢狱,苟求生活,不亦鄙乎!” 饮下毒酒后,这位当世大儒倒在冰冷的青砖上,鲜血染红了衣襟。
这幕惨剧的始作俑者,正是时任中书仆射的宦官石显。而站在石显身后的,是西汉王朝第十一位皇帝 —— 汉元帝刘奭。这场看似偶然的政治谋杀,实则是西汉中后期皇权嬗变的缩影。当石显的党羽们弹冠相庆时,没有人意识到,一个让后世史家痛心疾首的 “宦官乱政” 时代,正随着萧望之的死亡悄然降临。
宦官崛起:从刑余之人到帝国权臣石显的发迹史,堪称中国古代宦官专权的教科书式案例。这个济南籍的刑余之人,少年时因罪受腐刑入宫,从最低级的中黄门做起,凭借 “巧慧习事,能探得人主微指” 的本领,逐步爬到中书仆射的高位。
汉元帝即位初期,中书令弘恭与石显形成权力同盟。他们利用汉元帝 “柔仁好儒” 的性格弱点,以 “精通律法” 为由掌控中枢机要。公元前 48 年,萧望之等辅政大臣提出 “罢黜宦官、重用士人” 的改革方案,直接触怒了石显集团。史载石显 “内深贼,持诡辩以中伤人”,他联合外戚史高,以 “离间皇亲、结党营私” 的罪名构陷萧望之,最终导致这位帝师饮鸩自尽。
展开剩余77%萧望之死后,弘恭病死,石显顺理成章接任中书令。此时汉元帝因长期患病,已无心处理朝政,竟将 “事无大小,因显白决” 的大权拱手相让。石显趁机编织起庞大的权力网络:中书仆射牢梁、少府五鹿充宗成为他的左膀右臂,长安坊间流传的歌谣 “牢邪石邪,五鹿客邪!印何累累,绶若若邪!”,正是对这一宦官集团的辛辣讽刺。
帝王心术:汉元帝的权力悖论汉元帝为何对石显如此信任?这要从他特殊的成长经历说起。作为汉宣帝与许皇后的独子,刘奭自幼目睹宫廷斗争:母亲被霍光妻子毒杀,自己差点死于霍皇后之手。这种阴影让他对朝臣产生深深的猜忌,转而将 “中人无外党” 的宦官视为心腹。
这种畸形的信任,在萧望之事件中暴露无遗。当石显以 “谒者召致廷尉”(即逮捕入狱)的专业术语欺骗汉元帝时,这位熟读经书的皇帝竟不知其真实含义,稀里糊涂批准了逮捕令。待萧望之入狱后,元帝虽 “涕泣不食”,却仅对石显 “免冠谢而已”,最终导致悲剧无法挽回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痛斥:“人君者,察美恶、辨是非,赏以劝善,罚以惩奸,所以为治也。元帝两责而俱弃之,则美恶、是非果安在哉!”
更令人瞠目的是,汉元帝对石显的纵容已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。某年石显奉命出宫办事,故意请求皇帝特批 “夜开宫门”。待他深夜返回时,果然有人弹劾其 “伪造诏命”。汉元帝却笑着将奏章递给石显,任其表演 “伏地痛哭” 的苦情戏。这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秀,彻底消除了皇帝对石显的最后一丝疑虑。
帝国崩塌:石显乱政的连锁反应石显专权的十五年间,西汉王朝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。他通过 “持诡辩以中伤人” 的手段,将反对者一一铲除:魏郡太守京房因推行 “考功课吏法” 威胁其利益,被诬以 “诽谤政治” 处死;御史中丞陈咸因揭发其罪行,被判 “髡为城旦”(剃发服苦役);就连出使匈奴、签订 “汉匈世和” 盟约的张猛,也被逼自杀于公车署。
在石显的操控下,朝廷上下形成 “公卿以下畏显,重足一迹” 的恐怖氛围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等重臣为自保,纷纷 “阿附畏事显”,甚至助纣为虐。更讽刺的是,石显为洗白恶名,竟将名儒贡禹推举为御史大夫,上演了一出 “宦官捧儒生” 的政治闹剧。
汉元帝的不作为,让西汉的边疆与民生也陷入危机。在海南岛叛乱问题上,他听从贾捐之的建议,放弃武帝时期设立的珠崖郡,开了中原王朝主动弃地的先例。对陈汤、甘延寿 “矫诏灭郅支单于” 的壮举,他虽内心赞赏,却因畏惧石显阻挠,仅给予象征性奖赏,寒了将士们的心。
血色黄昏:石显集团的覆灭公元前 33 年,汉元帝驾崩,汉成帝刘骜即位。失去靠山的石显瞬间从权力巅峰跌落,被调任长信宫太仆,明升暗降剥夺实权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见风使舵,立即上奏弹劾其 “专权擅势、大作威福” 的罪行。
这位曾权倾朝野的宦官,最终带着妻儿老小踏上回乡之路。史载他 “忧懑不食,于途中病死”,其党羽牢梁、五鹿充宗等皆被贬谪边远郡县,长安百姓传唱新歌谣:“伊徙雁,鹿徙菟,去牢与陈实无贾!”
石显的倒台并未终结西汉的衰落。汉成帝比其父更昏庸,外戚王氏趁机崛起,最终酿成王莽篡汉的悲剧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总结道:“汉家之衰,始于元帝,成于成帝。”
历史审判:谁该为 “倾乱汉朝” 负责?石显之乱的本质,是皇权异化的产物。汉元帝将 “中人无外党” 视为金科玉律,却不知宦官集团的利益与皇权并非天然一致。正如《汉书》所评:“弘恭、石显以佞险自进,卒有萧、周之祸,损秽帝德焉。”
后世史家对此有深刻反思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指出:“石显之奸,非能浊乱天下,而元帝之柔暗以成之。” 他认为汉元帝的 “柔仁好儒” 实为 “迂腐无能”,其 “牵制文义,优游不断” 的性格,才是导致宦官专权的根本原因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,汉元帝并非毫无识人之明。他曾对太子刘骜的荒淫不满,一度想改立多才多艺的山阳王刘康,但终因 “犹豫不决” 错失良机,为西汉灭亡埋下伏笔。这种 “知善而不能用,知恶而不能去” 的矛盾,正是其统治悲剧的缩影。
结语:权力的镜鉴石显与汉元帝的故事,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一面镜子。它警示后人:当最高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时,任何制度设计都可能走向反面。宦官专权、外戚干政、权臣擅权,本质上都是皇权失序的衍生品。
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,长安城那片浸透萧望之鲜血的青砖,至今仍在诉说着权力异化的代价。而汉元帝那句 “乱我家者,太子也” 的临终叹息,不仅是对儿子的失望,更是对自己治国失败的深刻忏悔。
发布于:山东省加杠杆的股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